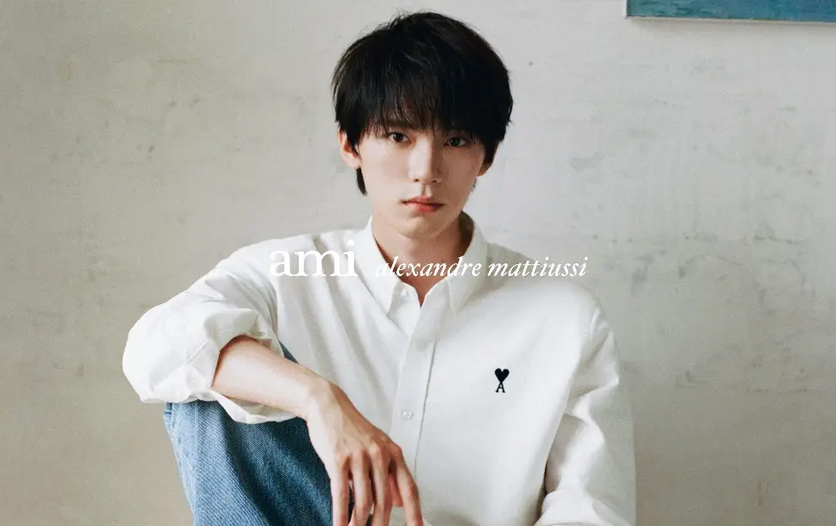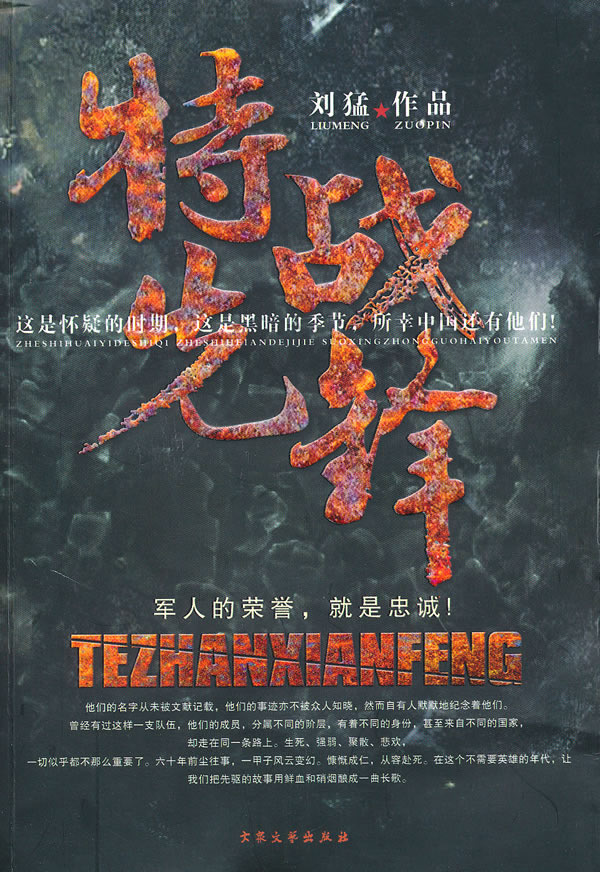
特战先锋
黄颖
摘 要:北村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作家,最初以一系列先锋小说步入文坛。《披甲者说》是他一系列“者说”中的历史传奇小说,在小说的叙事艺术上具有实验意义。本文从叙事视角、叙事语言、叙事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着手,细读和解析《披甲者说》,探讨北村小说的先锋意识。
关键词:北村 先锋小说 叙事艺术
《披甲者说》讲述了战争结束十四年后,福宁镇总兵吴万福、副总兵黄大来及众士兵庸碌繁琐的人生。小说并无精彩出奇的故事和高大传奇的人物,作者却仿佛沉浸在叙述和语言的游戏中饶有趣味,把故事描述得特别繁琐冗长。
一、视角转换和多重文本
叙事视角的选择会从形式上影响小说的叙事面貌。著名学者申丹将叙事视角分为四种:一是零视角(非聚焦型),即传统全知全能的视角;二是内视角,即故事中人物的有限视角和心理声音;三是第一人称外视角,即故事中作者之外的叙述者“我”的视角;四是第三人称外视角(外聚焦型)。北村的《披甲者说》这篇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外视角,这种第三人称视角有别于传统小说的“上帝”视角,它是从小说的四个主要人物:福宁镇总兵吴万福、副总兵黄大来、林稿房和寺庙住持法仁的视角来连缀故事,是有限制的视角;又有别于内视角对人物内心声音和情感的表达,它专注于对人物描写和故事发展的客观叙述。
这种限制叙事易造成小说的神秘效果,读者的所见所闻是故事中人物的所见所闻,故事展现的内容基本上是故事发生时间的内容。在有限的视角下只能看到单方面的景象,读者仅能从小说表层的叙述去推测和解读小说。另外,传统的小说都以时间为线索叙述故事的起因、经过、高潮和结果,《披甲者说》则从人物视角出发来叙述故事,并以此推动情节发展。比如“在吴万福来看……”“在黄大来的视线里……”“有这样一种情境……”“又有另一种情境……”很明显地把人物视角拎出来。小说的发展脉络是模糊的、不确切的,读者只有跟着小说人物的眼光,才能感知到故事的演进,从而陷入作者的叙事迷宫。
文中叙事视角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多个人物视角共存,且各视角自由转换。就像影视艺术的镜头切换一般,在不同的视角下看到的场景是不同的。小说以主要人物的视角连缀故事,但也往往出现时间重合、叙述重复的情况,比如小说开头写到吴万福和黄大来骑马上狐山,写黄大来的视角:“黄大来的坐骑顶着风打转,马蹄像烫着似的在坡地上腾起和回落。它敲响了宁静的山谷。在他吃力地跟上吴万福的一些时光里,吴万福的坐骑已越走越远……”吴万福的视角:“在吴万福看来,黄大来和他的坐骑越来越远,圣水寺红色的檐角隐约可见。”两者在叙事顺序上一前一后,叙事时间上有长有短,而事实上故事时间是相同的。由于视角的变换,使得叙事重复,北村的小说产生了“双重文本甚至多重文本的现象”。或许北村的目的在于从多个角度展现事物的各个侧面,从而更加完整地透视事件。但以时空的错乱和逻辑的断裂为代价的叙事,反倒使事物的面貌更加支离破碎和缥缈模糊,打破了故事的整体意义。
《披甲者说》通过多人物视角叙述故事,是北村对小说形式的有意识的探索,但他的实验不止于此,甚至有时玩起了叙述游戏。比如一个视角中包含多个视角,多个视角同时呈现,“黄大来在一些楠木树林后面发现了他,他和法仁和尚相对而立的情形类似交谈,其间熟稔的神情令人惊讶。在他们的身后,民工和和尚在砍伐楠木……在吴万福的眼里,民工砍伐大树的操作简单得无以复加……法仁看见那个砍倒大树的民工还沉浸在操作结束带来的快感之中。他还看见吴万福悄悄走近了那个民工……”其实无非在描述同一个场景,北村却把在场主人公的视角都写了出来,刻意强调人物的在场。这跟巴赫金的“复调小说”是有区别的,它并不展现人物的多样的声音,由于人物视角的限制,小说叙事只流于表面的感觉经验,主人公的内心思想处于失语的状态。从创作意图上来说,北村这么写并无主旨方面的意味,仅仅是形式方面的先锋。
二、语言迷津和真相的消解
语言是先锋作家们创作实验的关注重点。北村的先锋小说语言散漫、没有边际,跟随人物不断游走,人物眼光停留的一瞬都会被细致描述,故事旁枝逸出,让人陷入模糊虚幻的语言迷津。北村曾说:“语言要让它奔跑起来,并不是说我要诗化语言,我觉得应该是说人跟他所存在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了,这种变化体现为结构的变化。语言本身是很质朴的,但在它描述真相的过程中有可能把真相完全消解。”
《披甲者说》没有逻辑连贯、意义完整的故事,语言琐碎平淡,记录的是远离战争的军队的繁琐的日常生活。在北村笔下,一个原本简洁清晰的事件,在反复的解说下,变得游离模糊、惶惑不清。比如“黄大来是在一个太阳天进入睡意的,当时林稿房正在进餐,他细致地吃尽了一把未熟的芹菜,嘴里发出菜刀切断根茎的声音……林稿房把毛笔扔在砚台上,手指塞进嘴里,剔除了齿间的一根菜丝……”北村非常执着地细述这些繁琐的日常场景,把叙事时间无限拉长,造成细节的延宕和情节的搁置。它们在故事情节和叙述逻辑上完全没有提及的必要,只管随着人物的视角延宕开来,话语堆叠,空洞无物,一不留神就让人迷失在这些细碎里。
前面讲到该小说的叙事视角就是人物视角,而小说的叙事话语也尽量还原人物语言,与人物角色相衬。比如,吴万福视野中的路程度量是“一箭之遥”;在黄大来听来,“单调的木鱼声仿佛在摹仿迟逝的马蹄”。另外还有小说语言的陌生化。北村不仅仅试验词语运用的陌生化,还尝试语序的重新编排,打破常规句式。比如“在阳光下几乎睡着的张弩队手握锈蚀的箭链,嘴在阴影里一言不发的全副仪仗像没有脸的风沙遮盖了吴万福的眼睛”,原本吴万福是看的主体,而语序打乱后,人变成了行动的承受者。小说中这样的句式很多,物变成行动的主导,人的主体地位下降甚至物化。即便小说是有关人物视角的描述,但作者仿佛只是借用了他们的眼睛,所有人物都是被描写的对象,我们只能体会到表层的感觉经验,而陌生化词语的堆叠,让读者与之拉开审美距离,增加了玄幻感。
小说存在大量人物视角下的纯写实描述,语言客观冷漠,不含人物情感意志的温度。比如传令兵是“东倒西歪”的、建庙宇的人“像虫子一样忙碌”等。先锋作家试图反叛传统肯定的一切,对事物的认识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使一切问题的解释留有余地,充满阐释的张力。《披甲者说》的语言,语义模糊悖谬,比如“马鞍上的骑手双手抵着马背,单薄的身体向后倾斜,仿佛被风吹倒或者几乎落马,昂起的头的和直挺的下巴上的胡须,注视着苍穹上的一朵云。在黄大来的视线里这是一匹下山的马,而实际的情形是:吴万福身披绿缎斗篷,手执银鞭,策马上山。”运用“仿佛”“或者”“几乎”“而”等不确定性和否定性的语言,似是而非,让人在真实与虚假、现实与叙事中迷失。
三、交叉时空和循环叙事
北村的叙事深受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他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他们的影子。北村在接受访谈时曾说:“我们是从哪里走出来的?是从博尔赫斯走出来,从卡夫卡走出来,从海明威走出来,从里尔克走出来,我们从所有的现代派走出来。”博尔赫斯的时间观给予了先锋小说家深厚的启示,他认为时间是多维的、偶然的、交叉的、非线性的,在时空交叉织成的时间网里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
传统的叙事作品都是以时间为线索记叙故事,而在北村的小说中时间是不确切的,时空是交错的,打破了传统的叙事顺序。《披甲者说》开篇,把故事虚设在“清康熙十五年阴历九月初七,黄昏”,而事实上小说故事并没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它几乎可以放在古代任意一个时间点。叙事的时空是交错的,“在一丛迟开的晚香旁边,他们遭遇了一个饥肠辘辘的老道,当时父亲正撩开袍子,对着那丛晚香小便,风声灌满了他的耳鼓。老道在早些时候,在山上看起来只是一个黑点,他吃力地爬上山坡,风沙塞满了他的嘴。当老道东倒西歪地走到一棵刺松下的时候,夕阳已经下山。”在这里,小说采用倒叙的手法,叙事结束后,时间回到故事起点。又比如,小说叙述吴万福和黄大来在山谷的相遇,分别从两个人的时间线做了细致的描述,使叙事重复。这里刻意用重复消解时间的流逝,增加叙事细节的延宕感,使得感知模糊,真实变得虚幻。
《披甲者说》描述的是时间的一个轮回,一切都在篇尾揭秘。小说末尾有一段文字耐人寻味,“军营的凋敝开始于日前来临的一场台风,失信的消息再也不能取悦于士卒,直到大风刮走了他们手中的画角。”十几年来,军队一如往常地预测天气,然而所谓台风将至的消息却总是不准,已经失信于士兵,大家都没有做台风防范,最后台风来临,席卷了军营,军营凋敝了,一切化为废墟!“眼下,台风已过,受伤的马匹在路上哀嚎,战事的景象重新来临。”一切都重新开始,回到原点,终点的尽头也就是起点,周而复始,没有完结,仿佛一个又一个轮回。整篇小说就是在圆形时间下的循环叙事。
有学者将北村的一系列“者说”的叙事模式概括为“逃亡—迷失—死亡”路径,在《逃亡者说》《归乡者说》《劫持者说》和《聒噪者说》中,都有关于“逃亡”和“追捕”的情节。这种模式在《披甲者说》中不太明显,没有现实的“逃亡”,或许有对精神空虚的逃亡,但“迷失—死亡”模式却贯穿全文。吴万福作为福宁镇总兵,在远离战争后,十四年庸碌琐碎的生活使他迷失了自己的价值追求;副总兵黄大来总是一味地模仿吴万福,在吴万福去世后,没有真才实学的他面对军务却无所事事,患了精神病,自我迷失。吴万福在迷失中寻求佛的庇佑和精神皈依,捐钱修寺庙和生祠,最后寺庙和生祠毁于一旦;黄大来以对吴万福的崇拜来添补内心的空虚,吴万福逝世后却无所用心。他们精神游离、萎靡不振,最后都被箭射死了。他们的死并不是必然的,他们为什么死的,小说没有告诉我们确切的答案,而是留下了巨大的疑问和阐释的空间。但是他们在琐碎的生活中已经迷失很久,久到绝望了;在绝望的尽头,死亡是人物最后的归宿。
四、神性的消失和人性的萎缩
由“披甲者”,我们自然会联想到驰骋疆场、威风凛凛的将军,然而小说中的几位将领,父亲是“常败将军”;身披铠甲、头戴红翎的吴万福和黄大来就像“塑像”“瓷人”,没有英雄的印记。小说的故事特别沉闷,北村没有选择风驰电掣、戎马倥偬的战时场景作为叙写对象,而是从远离战争十四年之久、毁灭前夕的庸俗日常着手切入。这时的将军不像将军,士兵不像士兵,他们是疲懒懈怠的,没有勇猛刚健的气概和体魄,反而像虫子一样蚕食着千疮百孔的现实。北村颠覆了传统小说中对英雄形象的描绘,“他在普通生存个体身上悄然剥开生存的本来面目,露出了荒诞的、残酷的黑色背景。”
吴万福是十四年前那场战争唯一的幸存者,“他的军队击退了数千名敌人。他骑着一匹老马走到一棵刺树下,枪伤的疼痛使他落马,他在刺树的阴影下睡着了。清晨,一匹临死的伤马的哀嚎把他唤醒,当他重新踏上马蹬时,他发现尸横遍野的山谷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一觉醒来成了一个胜利者。以往打仗,士兵在城墙下厮杀,而他和黄大来在城楼上下棋煮茶。偶然一次被俘虏,居然意外地被放了出来。吴万福的胜利和幸存都充满着嘲讽戏谑和黑色幽默。
他平常“严行部勒,详申军律”,但又克扣军费去修建寺庙和生祠,这和军队精神是相背离的。而无事可干的士兵们都在忙着屯田种地收小麦,战争对于他们太遥远,他们已经分不清镰刀和弓箭,点名和阅兵只是走过场,刀枪箭镞有的锈蚀,有的被炼制成了农具、炊具。“战争对于他们只是个传说,他们中的一些人从年老的父母口中听到了零星的关于英雄的故事,已被漫长的从军岁月淘洗干净。当他们第一次穿上戎装,拿着长枪时,也许能回忆一些残缺的片段:衣着开裆裤,看着纷乱的马蹄掠过地上的簸箕、倾散的谷物和犁刀,那些闪动的刀影和人的影子,笼罩在马蹄激起的尘土中。在踩烂了肚肠的牛身上,聚集着苍蝇和牛虻。这些印象如同水中断开了纸,随流而去。”就连赋予他们社会价值和精神依托的战争,在他们视线里也不过是充满腥味和血污的“战争垃圾”;神圣崇高被解构殆尽,人寻求的生命意义丧失,神性消失。
黄大来是军队的副总兵,一直跟在吴万福的后面,模仿着他,学他骑马的姿势,练习用手指夹住飞箭的技能……“当他看见吴万福纵马从他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空虚像瘟疫一样淹没了他。”在吴万福去世后,“黄大来心事缥缈,他像一片风中的树叶,在离开枝头的瞬间陷入了迷途。”他的主体意识特别的低弱,“精神灵魂被抽空”了,行尸走肉般活着。另外,小说中人与人之间只有少许的语言交流,都是冷漠的旁观,吴万福的逝世在士兵中并没有激起波澜,而黄大来的上任对他们也无所谓,甚至黄大来最后射死了法仁住持……人和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让人心寒,连生命也被漠视,人性萎缩。北村说:“由于地位的失去,由于中心的匮乏……我不得不描写了一种没有意义的生活,在这种没有意义的危机中,人像活物一样各从其类,唯独无法很好地像个人。”
北村的先锋小说语言散漫冷漠、支离破碎,在时空的交错中营造叙事的迷宫,自我迷失在叙事技法里面,太过关注形式的陌生化,而忽视了文本精神的内化。另一方面,他大胆颠覆传统和常规,解构神圣和崇高,在重复、模仿、循环、反讽和陌生化等形式实验中,描绘凡俗的生命个体,展现人物空虚、恐惧、绝望的生存困境,追寻生命的意义。中国先锋文学的发展,跟先锋作家们积极担当、勇于实验的先锋精神密切相关,北村的形式实验值得肯定。苏童曾说“北村是真正的先锋派”,就在于“北村是很明确、自觉、执着地进行‘先锋性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于京一.远逝的先锋——北村小说论[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3] 蔡惠英.从废墟中升起救赎的王国——论北村关注存在的写作[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 北村,郭素萍.写作是生命的流淌——北村访谈录.北村博客,2005-10-26.
[5] 修彬.先锋的迁移——北村小说作品讨论会综述[J].福建文学,1995(1).
[6] 北村.施洗的河·我的大腿窝被摸了一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7] 陈晓明.北村的迷津[J].当代作家评论,19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