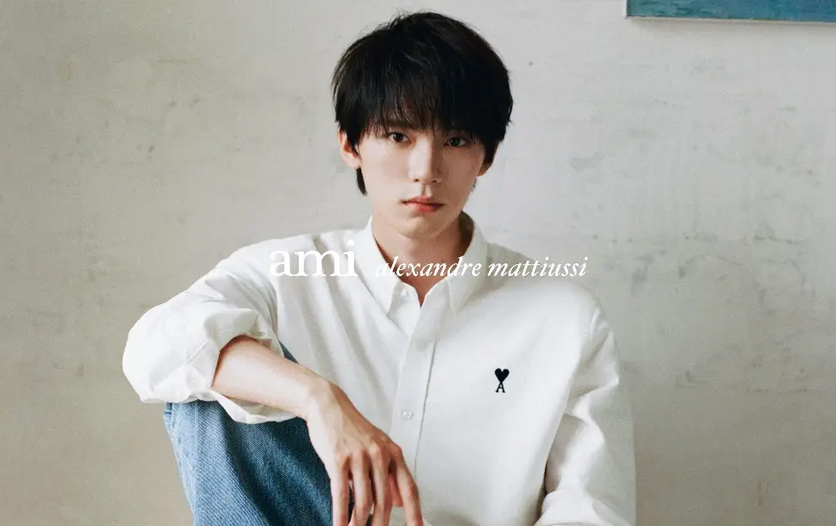范雅楠
摘 要:苏童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其作品创作是当代文坛一抹靓丽的异色。苏童笔下描绘的常常是充满欲望和暴力、人性受到抑制的带有南方情调的灰色生活。他将现代颓废与中国古典美学巧妙地交融在一起,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独具一格,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国内众多的“先锋派”小说家中,苏童是将瑰丽的创作想象与浪漫的颓废美学结合得最为完美的一个,暗浮的宿命论断、奇异的地域风貌和工笔唯美的语言特征,构成了苏童颓废美学的核心点。
关键词:苏童 颓废气息 《米》 颓废意象 叙事艺术
一、生命轮回中充斥的颓废气息
文章背景向来模糊暧昧。有时候生活里一件鸡零狗碎的事情,比如一双回力鞋、一把花雨伞,就足以演绎一个短篇。但他的文字里有无限乐趣,就像他常有的那种人物之间的冲突,写尽人性的剔透表现。
(一)宿命的轮回
苏童的第一部长篇作品《米》,讲述了一个关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毁灭的故事,在思考和展示人的命运中的黑暗面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毁灭之后的重生之美。《米》的主人公五龙是一个逃离饥荒的农民,他远离了枫杨树他的家乡,通过扒火车的方式来到了城市。生活在枫杨树的五龙,对米怀着一种近乎痴狂和变态的偏爱,当他来到城市,来到码头,伴随他的是一把家乡出产的糙米,无论地点怎样变换,伴随着五龙的命运始终不会有所改变。当五龙终于在城里站稳脚跟之后,命运的轮回再一次倾轧而来。作为枫杨树的逃亡者,五龙一方面始终怀有对农村根深蒂固的“恋根情节”,另一方面对城市所发现的罪恶世界抱着对抗性的疏离。“我是这米店的假人,我的真人还在枫杨树的大水里泡着。”尽管他占有了米店的产业,占有了米店的姐妹,占有了子孙满堂的家,占有了一个大码头,但仍像飘忽不定的游魂。他没有归属感,没有存在感,仿佛一个空壳一样,只有空洞洞的肉体,却丧失了灵魂。与《罂粟之家》的长工陈茂不同,五龙在农村未曾受地主直接的凌辱,枫杨树也是一块相对安全的净地,当带着自由主义的淳朴的天性进入这座到处充满污秽和罪恶的城市,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恐惧感、受辱感时时压迫着他。五龙和《骆驼祥子》里祥子的命运很相似,但是祥子最后毁灭的只是他自己,祥子最初仍然葆有最初的纯真,支撑着他渡过一次次困难。五龙却从第一次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就抛弃了农民特有的天真,路灯下的死人从最开始就提醒着他这个世界的丑恶和荒诞。他将米店闹得天翻地覆,将码头兄弟会闹得天翻地覆,将自己的家闹得天翻地覆,也将自己的生活和生命闹得天翻地覆。然而,这一切就像五龙发迹之后将一口“能清脆地嚼烂生米的好牙”全部都敲碎,然后换成一口金灿灿的金牙这一事件一样,仅仅表现了五龙那没有归属的存在感,满含自卑感的痛苦的心情。这种心情非常复杂。他的存在感只表现在手里真实到可以碰触可以把握的白花花的大米上;也只有在米上,他才可以回归最原始的野性和欲望。
一个复仇者的毁灭,总会给作品涂上悲壮色彩。当五龙最后由于报复而染上了脏病,自己的儿子像他一样缺少人性、人情淡漠之时,没有存在感仿佛游魂般的五龙决定还乡。他装了“一车最好的白米”回家乡,这似乎圆满了他大量占有大米的梦想,也似乎是对乡村生存焦虑的一种消解。五龙的人生是由城市的罪恶和对家乡的怀念这两部分构成的,他赤条条地从乡村来,仅有的财产就是一点家乡的大米,然后又赤条条地回到乡村去,这次伴随他的是一车皮的大米。他在物质上富裕了的同时,内心却更加空虚和痛苦,并且还没有看到自己辉煌的那一天,而是死在了自己引以为傲的一车大米上。这种宿命般的呼应体现了深刻的悲剧色彩,也展现了苏童用颓废的语言和颓废的故事以及伴随故事发展的颓废的环境,表现出一种宿命论的因果轮回。
(二)残缺与麻木的心灵
残缺与麻木描述的不是一种静止心理状态,而是一种不断重复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长期受迫害累积下来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这种因受到伤害而形成的自我保护模式也会伤害到他人。“一个人内在精神的残缺与麻木越严重,他的基于自卫与复仇愿望的爆发性和毁灭性也越强。”
五龙和小拐便是这种苦难逻辑的最好体现。五龙在长期的忍辱负重中受到严重的精神扭曲,在终于取得权势和地位之后,“他的各种畸变的本能与破坏欲望也就同时找到喷发的契机。他本能的破坏性由自我转向外部世界,以变本加厉的施虐方式补偿曾经受虐的缺憾,甚至连妻子和情人也成了他复仇发泄的对象,这种破坏性的报复似乎成了他全部人生的内容。”在《刺青时代》中,身体上的残缺使小拐的心灵更加扭曲,他眼中的世界已经变形,其中充满暴力与血腥。他不失时机地制造流血事件,冀图将这个世界变得与他一样的残缺。小拐和五龙都从一个备受摧残、伤痕累累的受难者变成了残暴的复仇者,复仇又必将带来更多的灾难,他们自身则会成为复仇最大的受害者。在无休止的生命轮回中,残缺与麻木是人从世界堕落开始的,一旦失去了对生命美好的追求,孤独和绝望便汹涌而至。
二、意象中表现的颓废气息
苏童作品中向来缺少明媚阳光和积极向上的意象,而多是一些灰暗低沉、缺乏生气的意象。在苏童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美丽总是与丑恶联系在一起的,在读者或者其他作家的眼中可能是美丽的东西,但是到了苏童的笔下,却往往都加上了颓废的气息和毁灭的意味。
米,一种深具南方意义的典型作物,作为作品中的主题意象,出现在了枫杨树这个苏童笔下典型的南方地带。只要能插秧,就可以看到米的踪迹,可以说米和枫杨树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一开始,米这个意象就出现在故事中,忍饥挨饿的五龙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所熟悉的只有枫杨树家乡的大米,也只有这些仅存的米,让他能继续生存下去。然后,五龙走进了一条巷道,进入了他未来生活发迹并走向毁灭的米店。五龙一心想征服城市,为的是报复自己曾经承受的屈辱。但是他渐渐地发现,这个城市到处充满了黑暗的罪恶和丑陋,而自己渐渐地和这城市的丑陋融为一体变成了城市黑暗的一部分。五龙在城市的生活起始于大鸿记米店,也是他在城市生活的落脚点和故事发生的起点。而米店一家人和五龙的纠缠贯穿于整个故事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五龙先后和绮云、织云之间的婚姻生活,也体现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五龙爱米胜于爱女人、爱一切。米也给了五龙发迹最终成为米店第五十四代传人的机会。他靠一担大米在黑道上发了迹,变成了一条恣意妄为呼风唤雨的地头蛇。米给了他元阳和精气。他经历了无数的淫乱生活,染上了让人厌恶的花柳病,以至于最后奄奄一息失去了人样,又变回了那个让人厌恶让人瞧不起的五龙,但是散发着米香的大米却给了他无穷的灵感和精力,去打倒一个又一个对手。
苏童写米,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米所带来的饱腹和温暖,而是伴随着五龙阴暗颓废的一生;米的变化,也是五龙生命的轨迹。在苏童的作品中,米所呈现出的也不是圣洁的白色,而是挣扎在绝望边缘的灰色,这灰色也在五龙的一生拼斗中沾染了血腥的味道。米所包含的颓废性的含义,暗示着颓废越深,离最后的审判越近。
三、苏童作品的叙事艺术分析
苏童作品中的人物性格都有一种沉郁、阴暗的特色,而他的小说,总是以细致绵密的抒情性想象见长。在苏童的书中,总是可以发现,他的故事都和南方的城市、南方的生活紧密相关,不论是其中的意象、意境,甚至是修辞和语言,都带着南方特有的绵密的特性。苏童小说中的一些美学特征,都是借助南方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得到展现的。不同于北方一马平川的辽阔广袤、金戈铁马的荡气回肠,南方应该是小桥流水的温柔雅致、深门大院的哀婉幽怨、老街弄堂的杂琐民事、温软嗲嗔的方言俚语。可是,苏童的南方世界却给读者呈现了一个人性丑陋、潮湿阴暗的画面。在南方的炎热和潮湿中,所有的植物和霉菌都在疯狂地生长,人却在霉菌和雨雾中感到压抑和窒闷,受到黑暗的欲望和肮脏的骚动的折磨。但是,在这炎热与潮湿、黑暗与肮脏中有一份沉重的真实,对苏童构成诱惑的最主要的因素也许就是南方的真实。
四、总结
苏童作为中国当代文坛“先锋派”的代表作家,其作品风格独树一帜,独领风骚。他的作品中蕴含的独特的颓废气质、颓废的意象、颓废的语言和颓废的描写,发人深省,不同于其他“先锋派”作家以及历来的中国文坛的许多作品中积极向上的描写,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全方位地了解苏童及其作品,才能更好地读懂存在于苏童书中所描绘的颓废下的希望世界。对于苏童的创作,我们同样也能在了解他的南方世界的同时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深刻的反思;同时,研究其笔下的病态人物,探讨其中的原因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深入了解苏童的文学世界。
参考文献:
[1] 谢有顺.先锋就是自由[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2] 孔范今,施战军.苏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 张立群.先锋的魅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 陈传才.中国20世纪后20年文学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5] 王昭,郭悦.真正的先锋一如既往——苏童小说创作特色浅析[J].科教文汇,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