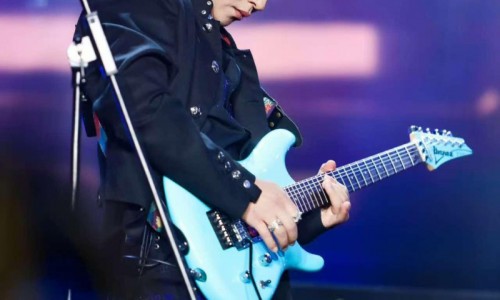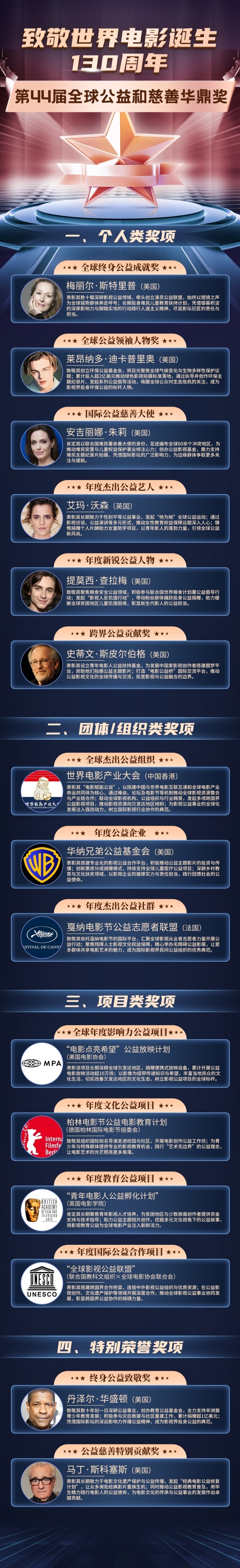誉者或损其真-我想是不是我妈妈代签了?经过核实,并没有. 我开始着急了,呵呵,...
顾晔峰
摘 要:《论语·侍坐》章是《论语》中最富于文学色彩的篇章之一。但多处训读颇有歧义,尤其是“夫子哂之”中“哂”的解读更是霄壤之别。本文首先分析了诸家训读的大致情况,再从语境学角度并结合孔子和弟子的人际关系来解读这个疑难之点。本文认为“哂”在其语境中当训读为揶揄的嘲讽,由此恰可以说明孔子首先是一个有着常人情感的普通人,孔子和诸弟子间是一种坦诚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后人对《论语》的误读、争论,多与神圣化孔子有关。
关键词:《侍坐》 哂 神圣化 语境
《论语·侍坐》章记录了孔子及其四位弟子关于各人志向抱负的一次讨论,是《论语》中最富于文学色彩的篇章之一。文章通过对人物语言及动作神态的记录,生动表现了孔子和几位弟子不同的个性风采。因此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文学成就上,《侍坐》章在后世具有重要的影响。但《侍坐》章多处训读存在歧义,莫衷一是,致使解读困惑。关于文中“夫子哂之”的“哂”的解读更是霄壤之别。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诸家“哂”的训读溯本清源,并从语境学角度,通过对《侍坐》章、《论语》全书等各个层次的语境分析,再结合孔子和弟子的关系来解答这个疑难之点,以求得更为合理的解释。
关于“哂”的解释,主要有四种训读:1.何晏在《论语集解》注引:“马曰:哂,笑。”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孔子为何种“笑”,笑的方式有很多种,因此也就没法弄清孔子对子路所说的话的态度。2.宋朱熹注:哂,微笑也。(《论语集注》)这一说法影响最大,多数学者持这一说法。钱穆先生则进一步认为:“孔子既喜子路之才与志,而犹欲引而进之,故微笑以见意。”{1}但这一说法和上下文内容明显不一致:下文曾皙就哂笑专门请孔子解释,如果只是微微一笑,曾皙也没有理由专门提请老师来就此说明。将“哂”训为“微笑”,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为圣人讳,即“万世师表”的孔子,对待他的学生怎能不是包容式的“微笑”?3.清代宋翔凤《论语说义》始指明“哂”并非是微笑:“《说文》:‘弞,笑不坏颜曰弞。从欠,引省声。《说文》无哂字,作弞为正,矧是假借。凡笑以至矧为度,过此则坏颜,且失容,故曰:笑不坏颜。“哂”非微笑之谓,曾皙亦以夫子有异常笑,故问之尔。”{2}宋氏于此认为“哂”是一种“异常笑”,非为一般的“笑”或“微笑”。但遗憾的是,宋氏并没有进一步指出“异常笑”的内涵是什么。4.康有为注:哂,大笑也。“哂”与“矧”同。《曲礼》:“笑不至矧。”郑注:“齿本曰矧,大笑则见。”{3}康有为据“哂”与“矧”同,其实不然,前文曾指出“矧”乃为假借,本字当为“弞”,即为笑不坏颜意。康有为据“齿本曰矧”,解“哂”为“大笑”,显然是不成立的。再则“大笑”也只是说明了笑的形态,还是没有说明笑的本质意义。
孔子之所以“哂”笑仲由,是因为仲由这样讲了一段话: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这段话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我子路能治理状况非常糟糕的中等国家,内有饥荒,外有大兵临境,过几年却可以让老百姓勇武。对于子路这个方面的能力,孔子丝毫不怀疑,孔子曾经这样评价子路:“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孔子还向季康子推荐子路说:“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意思是说子路果断干练,不拖泥带水,从政不成问题。问题就出在第二个层次“且知方也”。“方”,何晏注为“义方”。《论语正义》曰:“《广雅·释诂》:‘方,义也。郑注此云:‘方,礼法也。礼法即是义。《汉书·礼乐志》引此句解之云:‘教以礼谊之谓也。与郑注及此注同。《司马法》云:‘古之教民,必立贵贱之伦经,使不相陵,德义不相逾,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是其义也。”{4}在那样一个内忧外患之国,三年时间使百姓知礼仪懂教化,在孔子看来这是子路难以做到的。因为孔子认为,礼仪教化的事情,“尧舜其犹病诸!”——尧舜都是难以做到的。所以当曾皙问曰:夫子,何哂由也?孔子曰:“其言不让,是故哂之。”说明“哂”笑的对象是子路说话内容不知谦让。
我们认为本文中的“哂”就是揶揄的嘲讽、讥笑,原因有二:首先,如果孔子不是很明显地讥笑子路,后文中曾皙专门向孔子提出“夫子何哂由也”的问题就令人费解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由上下文寻绎,从当时的语言环境来看,孔子有意引导学生“言志”,“以观其才志”。但由于孔子讥笑了子路,这次座谈活动的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则,从活动形式来看,孔子本来希望大家自由畅谈,但因孔子的“哂”笑,会谈气氛骤然趋紧,孔子不得不点名提问;二则,接下来回答提问的冉有、公西华一个比一个更加谨小慎微了,尤以冉有的回答更能看出一些端倪。冉有所说的每一个分句都是缩小版的子路的叙述,子路说能管理“千乘之国”,冉有改成只能治理“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国家,子路讲“且知方也”,冉有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试想如果不是善于察言观色的冉有捕捉到了老师对于子路的嘲讽式批评,他也不会如此刻意地比照着子路的话来讲,尤其是“如”,让我们看到一个工于心计的冉有:冉有前面讲了可以治理“方六七十”的国家,寻思大概谦逊的还不到位,再一次改口说自己只能治理“或者五六十”的国家。这一改口,颇有深意,朱熹就此指出:“冉有谦退,又以子路见哂,故其辞益逊。”朱熹虽未说明“哂”的内涵,但却指出了冉有功利地修改回答内容的事实。其次,对待子路的这种率真、冒进,孔子的教育方法是“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就是在有些场合刻意地压一压子路的锐气。所以,这次子路在一路豪情下说出来“且知方也”,孔子讥笑他一下是很正常的,我们用不着曲为之解。
说孔子讥笑自己的学生,这并非是要颠覆孔子的形象,或者诋毁孔子和子路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孔子其人有一个逐步神话的过程,历史上的孔子本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真诚,坦率,喜怒哀乐往往形于表。梳理《论语》一些片言只语的记载,我们可以勾勒出孔子的本色状态,从中更能看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实际上是一群率真、可爱的人。李泽厚先生有一段非常中肯的评价:“《论语》中的孔子是生动活泼的活人,有脾气,有缺点。例如,虽然‘即之也温,但也常常骂学生,而且骂的很凶,‘其言也厉。但也经常开各种小玩笑,根本不像后世把他抬入神龛内的那副完美无瑕,却完全失去活人气息的木偶面目。”{5}《论语·阳货篇》记载,孔子的弟子子游在武城做地方官,孔子到武城去,听到有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其治小邑,何必用礼乐大道!孔子明显带有戏谑的味道,子游当即反驳:老师您经常教导我们说“君子小人以位言,在上在下皆当学道,子游言虽宰小邑,亦必教人以礼乐”。孔子看子游很认真,就立刻板起脸来说:弟子们,子游说得对,我刚才只是同他开个玩笑罢了!
孔子一生弟子众多,但本文中提到的四位学生中,孔子和子路的关系尤为特殊。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二人虽为师生,但年龄相差不大,子路“少孔子九岁”。子路在认识孔子前曾经“陵暴孔子”,然后孔子才“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质委,因门人请为弟子”。两人可谓不打不相识,从一开始子路与孔子更多的是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因此,两人在言语之间的诘难、冲突就在所难免了。《论语》中记载子路被孔子嘲笑并不鲜见,如“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意思是说,如果我仲尼离世隐居,能跟随我去的恐怕只有子路。子路听了很高兴。但孔子却接着又说:“仲由太好勇了,他好勇的精神大大超过了我,这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了!”朱熹注曰:“子路以孔子之言为实然,孔子美其勇于义,而讥其不能裁度于事理。”讥笑之意甚明。
反之,子路有时对孔子说话也很不给面子。有一次,孔子拜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南子品行不端,在当时口碑不好。子路觉得老师这样的人不应该去结识南子这种是非之人,因此很不高兴,当面就去责问孔子,弄得孔子不得不在子路面前对天起誓:我所行,若有不合礼不由道的,天会厌弃我,天会厌弃我!子路的执着,孔子的急于表白跃然纸上,就如同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雍也》)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说:“孔子被逼的没办法的时候,也只好对天发誓以表白自己,和今天的人一样,神态可掬。”{6}
总之,孔子和子路之间的关系非常特殊,在《论语》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孔子曾多次批评子路过于直率、鲁莽,甚至有时毫不客气地说子路“是故恶夫佞者”(《先进》),就是说我讨厌像你这样强嘴利舌的人。同样,我们也不时可以看到子路不留情面地对孔子指陈:“子之迂也!”这些言语上的辩驳、碰撞,不是说孔子和子路之间关系出了问题,反而更能说明孔子首先是一个有着常人情感的普通人,孔子和子路之间是坦诚的亦师亦友之情。后人对《论语》的误读,多来自于神圣化孔子的心态。我们在解读文本之时,如若拘泥于此,只会缘木求鱼而不可得。
{1} 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279页。
{2} (清)宋翔凤:《论语说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3} 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3页。
{4}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68页。
{5}{6} 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