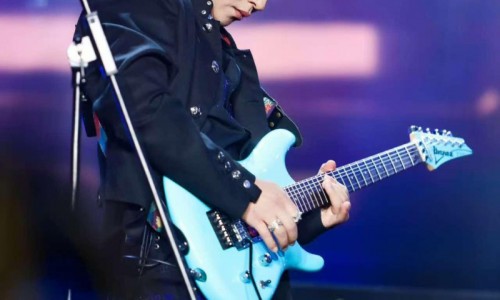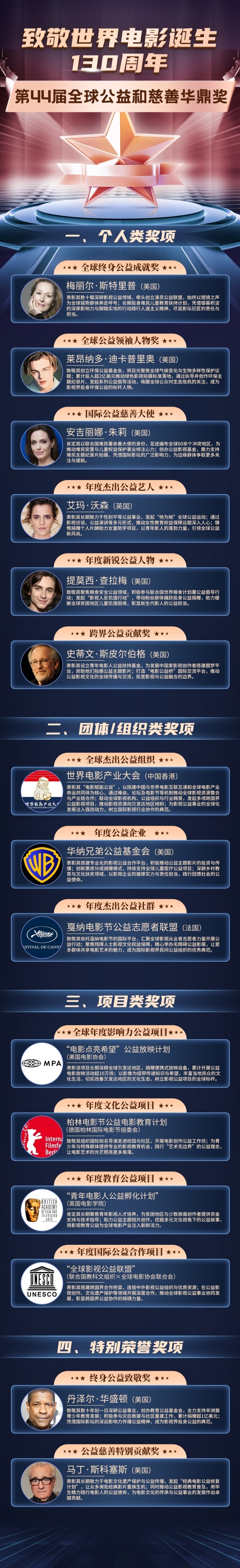与造物者游
何巧忠
摘 要:通过陶渊明的诗歌,本文以为陶渊明从来都在“与造物游”。他从悠然的田园生活到不为世俗左右、看淡世事,直至忘却世情无不表现出他的自由精神——“游”的心境。本文从入世、出世、忘世三个角度结合陶渊明的诗句解读了贯穿于陶渊明一生的“游世”思想。
关键词:陶渊明 诗歌 “游”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艺术的“自觉”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争鸣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往往通过文学的形式来表现对人生哲理的深入探索,然而玄言诗的广泛流行,使得文学艺术内容显得空虚狭隘。陶渊明以独到的观察事物的眼光把最平常的事物以质朴、平淡的笔调写出了不平常的诗意,所以远远地超出了同时代文人。通过陶渊明的诗歌,我们读出了他刚正不阿的人格,真率的生活态度,热爱劳动和田园生活的情操,执着探索人生真谛、不断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以及由此而体现出的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游世”的心灵。陶渊明以庄子“安时而处顺”{1}的思想,“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2}。他从田园走来又回到田园,他长时间的农民生活,使得他的诗歌融会了他对田园生活的种种体验和对人生真谛的种种思索。“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3}陶渊明有了“游世”的思想,那么是“隐”还是“仕”,就不在乎方式,他将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人生巧妙地融合起来了。他的诗歌所体现出的“寄意于物”“游于物外”的自由精神,是陶渊明精神面貌的体现,是他的田园诗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一、入世之游
陶渊明和所有的人一样,生活在庞大而又复杂的现实世界之中,面对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艰难困苦以及在仕途上与自我格格不入的尔虞我诈,他能有所超越吗?从陶渊明的本性出发,他从小就热爱着那片土地,由此而将自己半生时间参与躬耕。陶渊明既喜爱田园又要“大济苍生”(《感士不遇赋》),所以他经历了屡仕屡隐的一生。这对他来说,是从自然走向仕途,又从仕途返回自然。从此,陶渊明固守着那片土地,并怡然自得。从他对田园风物由衷的喜爱和深切的依恋,我们可以体味出诗人那纯净的心地和平静的心境,他显然是与简朴恬静的田园风光交融在一起了。陶渊明热爱劳动,喜爱田园生活,并将率真的自我灌注到造物里,即所谓“寓意于物”,把最真我的性灵畅游于那片土地之上。
(一)“性本爱丘山”
之所以能从陶渊明的诗歌中感受到恬淡的意境和朴茂的生机,和他小时候的经历以及与生俱来的天赋息息相关。陶渊明从小生活在临近鄱阳湖、庐山的浔阳柴桑的乡村之中,朝夕接触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色。他生活的时代,又是自然美感在人们意识中日益变得重要的时代,《世说新语》里可以看到东晋人赞美山水的许多名言隽语;老、庄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和美妙的寓言,《诗经》《楚辞》以及汉魏以来的诗歌散文中描绘自然的许多精美的片段,又给他以丰富的启示,所以他从小就喜爱自然。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是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与子俨等疏》),从中可见,陶渊明“爱丘山”“爱闲静”的与生俱来的热爱大自然的本性,往往让自己“欣然忘食”“欢然有喜”。这种喜爱是骨子里的,只有这样,才能将自我交给丘山。这为陶渊明以后走上归隐田园之路,写出质朴天然的诗歌作品,使自我精神世界得到满足奠定了基础。
(二)“聊为陇亩民”{4}
陶渊明长期生活在土地上,参与劳动。这种长期的农村生活成为他的生活体验,统统化为笔下“率真”“任情”的诗歌。躬耕田园的生活使他心情舒畅:登山临水、饮酒赋诗,与农民往还,使他感到充实、自足;火荒、歉收、疾病给他带来了困厄,使他有过不平的悲愤,但他都能以委运任化的潇洒态度泰然处之,安贫乐道。“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句子,正是陶渊明的独特之处。他把事物的客观存在,贯穿于自己的感情之中,“这种‘情不仅仅是一般的喜怒哀乐的情绪,而是具有深刻的内容,蕴含着诗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摸索和一定程度上的认识”。陶渊明的“情”是通过形象化的方式表现的,笔下的客观环境,其中人、事和物,都融入了强烈的主观感受和情思。崇尚自然的情怀和重返自然的喜悦在他的诗歌中常常出现,他那获得自由的典型感受就是心情十分愉悦。所以他笔下的那十几亩田地、八九间草屋、屋前屋后的桃李和榆柳,还有深巷中的狗吠、桑树旁的鸡鸣,以及那远处隐隐的村落和近处农舍上袅袅的炊烟,无不充满生机,趣味盎然。“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独游,欣慨交心。”(《时运并序》)当陶渊明走向田野的时候,心情非常兴奋。初春的鸟声显得格外的欢快,初春的和风也好像特别的轻柔。“平畴交远风,良田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不仅写出新生秧苗都在春风中欣欣向荣的生意,更洋溢着他看到自己劳动的初步成果时那种迫不及待的喜悦心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道:“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陶渊明在诗里写到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时得到的快慰,都很真切。“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写出农民很普遍又很深刻的感受。他的田园诗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淡、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如“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写山村的早晨,晨雾渐渐消失,南风使新苗长上了翅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写邻居和自己一起谈史论文的情形,那种真率的交往实在令人羡慕。这些作品只是陶渊明在娓娓道来,只是把他此时喜悦的心情说出来,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文字背后那种自由自在的心灵之旅。
二、出世之游
陶渊明和所有的传统文人一样,都想为民请命,那么他的“猛志逸四海”能实现吗?或者说陶渊明能兼济天下吗?的确,陶渊明有过自己的“仕途”生活,由于看不惯官场黑暗,他几次弃官以摆脱世事相约束。最终,陶渊明面对腐朽、庸俗的社会风气,官场的趋炎附势、尔虞我诈以及自己生活贫困的艰难处境,都能泰然处之,心境澄明。他选择了归耕,从而可以享有田园生活的自由美好。“风格即人”这条艺术规律,在陶渊明身上得到验证。他“脱颖不群,任真自得”(萧统:《陶渊明传》),不掩饰,不做作,不为世俗左右,我行我素,身心走进自然,精神融入自然又超越自然,思想上得到真正的净化和升华。
(一)“误落尘网中”
在我国古代从西晋、南北朝到东晋的这段时期,南北朝之间、北方各族上层统治者之间以及世族与皇族之间的斗争十分剧烈。这些斗争在东晋政权存在的一百多年中从未间断,酿成多次内乱,人民流离失所。其中有名的秦晋淝水之战和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就发生在当时。
陶渊明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政治极为黑暗、腐朽的年代。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至晋安帝义熙元年(405)的十三年中,陶渊明先后担任过祭酒、参军、县令等职。他性格正直耿介,与官场的腐朽风气格格不入,几次都是辞官而去。眼看“大济苍生”的宏伟抱负不能实现,他面临着一个矛盾:是和统治阶级同流合污呢?还是归田躬耕,求得洁身避祸?最后一次辞去彭泽令结束了他的仕途生活,“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5},在带有些许悔恨的同时,他终于可以“复得返自然”而真正走上“躬耕”的道路。他在精神上感到极大的解脱,心情也异常兴奋。庄子人生境界中的出世者,便是“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庄子认为,“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6}都是束缚人们心灵的桎梏,甚至连人的健康、智慧、愚钝也都是外在的东西,只有纯白朴素,至真至纯才是人的本性。怎样才能彻底摆脱人为的各种束缚,尽显出人的本性,使自我合乎自然之道呢?这就是通过艰苦的修养,达到“吾丧我”的境界。所以,庄子的隐逸是让人的心灵超乎俗世之外。
(二)“何事绁尘羁”{7}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其八),“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神、影》),陶渊明终究摆脱了人间世俗的种种羁绊烦扰,在精神上真正达到了与自然为一、自由自在的境界。庄子所谓“逍遥游”,乃是“无所待”的绝对自由。它“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于四海之外”,它“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于何有之乡,以处圹之野”{8},因而是一种人生最高境界,是真正的自由境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参透一切苦厄,把身外之物看淡,整治清扫心灵,达到虚静状态,豁达、潇洒,了无牵挂,无忧而有喜。这就是“出世”的思想。当人们进行认识的行为时,首先使自己的心灵达到极度的空虚,不持一点固有的成见,同时又达到一种沉着冷静的境界,而客观如实地认清事物的真相,这种心态,老子称为“玄览”。因为,心虚则无物不容,心静则察知万物,从而达到对“道”的认识和把握。所以此时,陶渊明笔下的农村田园风光很宁静,很美好。《时运》中所写,暮春时节,景物融和,独自出游,唯有身影相伴,欣喜感慨,交杂于心。“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下笔缓缓四句,正写出诗人悠然自得、随心适意的情怀。“称心有言,人亦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人们不是这样说吗?凡事只求符合自己的本愿,不为世间的荣利所驱使,人生原是容易满足的。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在朦胧醉意之中,我就自得其乐。陶渊明之热爱自然,内中还深含着一层人生哲理。在他看来,多数人由于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追逐无止境的欲望,于是虚伪矫饰,倾轧竞争,得则喜,失则忧,人生就在这里产生了缺损和痛苦。而大自然却是无意识地循着自身的规律运转变化,没有欲望,没有目的,因而自然是充实自由的,无缺损的。人倘能使自己化同于自然,就能克服痛苦,使人生得到最高的实现。《和郭主簿》诗里所描写的田园风光,虽然不过是正常农村中的寻常景物,但由于受到诗人理想生活的洗涤,所以一经入诗,都充满了无穷的情趣。在这里,它完全是一片诗化了的田园,其中的一景一物,无不饱含着诗人的无限深情。还有《移居》《读山海经》等诗,都可以看出陶渊明远离尘嚣,悠然自得,达到了畅游于无的境界,而无的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那就达到了游于道的境界。这,就是理想的人生境界了。
三、忘世之游
陶渊明充满矛盾的一生,在一定程度上是痛苦不堪的,那么面对这些痛苦他能做些什么呢?他饮酒和忘怀。陶渊明表面上借酒让自己脱离了现实,实际上他已经达到了“无所待”的心境。
他把酒的“消忧”(或者“忘忧”)作用看得很高。他曾说“酒能祛百虑”,“酒云能消忧”,“试酌百情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这里叙述陶渊明在日落鸟归之际面向自然,有所感发,快活得飘飘然,以至于“忘言”,也就是说达到了“得意忘形”的精神境界,其无心中又有心与物会,物我两忘之境,而人生之种种真谛已寓含其中,忘则忘矣,亦不须说、不必说,一切尽在意中。
(一)“不觉知有我”{9}
“渊明之诗,篇篇有酒”(萧统:《陶渊明集序》),鲁迅则说:“陶渊明在后人心目中,实在飘逸太久了。”{10}《陶集》现存诗文一百四十二篇,凡说到饮酒的共五十六篇。完整的饮酒诗就有二十多首。对此,陶渊明除了“性嗜酒”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写作动机呢?他的嗜酒与生活、写作有何关系?其饮酒诗反映了怎样的思想情调?陶渊明对于酒应是一种安于现状的麻醉,应该说这与他的不满现实并不冲突,“欲有为而不能”的他只好寄情于自己本来就热爱着的那片土地,而且生活上也还“退可以守”。他四十二岁从彭泽归来以后,写了《归去来兮辞》和《归园田居》,这些作品反映出的是他的纵情酣饮,不同于前的是此时他已经感到人生无常,要求及时行乐,以酒忘忧。到了六十岁那年,陶渊明得到酒友颜延之周济,又酣饮起来,有诗云:“我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又云:“我有旨酒,与汝乐之。”足见渊明是直到晚年,还在酣饮赋诗。既然他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得如此惬意,那么这个世界对他来说还有什么呢?“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神、影》),他委运任化,顺乎自己,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无论生活遭遇如何,他都没有激烈的情绪变化,没有巨大的感情起伏。在摆脱了建功立业的强烈追求和怀才不遇的悲慨等世俗束缚之后,他在宁静的田园中怡然自乐。“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他和自然完全融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人生之种种真谛均已蕴含其中,流露出陶渊明陶然忘机、怡然自得、平和淡泊的人生境界。
(二)“欲辨已忘言”
“每有意会,便欣然忘食”,“忘怀得失”,“晏如也”(《五柳先生传》),陶渊明拥有这样清虚恬淡的心态,形成了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的人生态度。庄子认为,只有“忘”才能达到“自适”的境界,故而提出了“坐忘”的概念。庄子的“坐忘”正是摆脱人生种种内外束缚,获得绝对自由,最终达到与道冥契的最佳方式,也就是心隐的形式。“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其八)此诗通过采菊泛酒,观鸟归林,写生活如何清静,心境如何淡远,只有过这样的生活,才会对眼前的自然意趣有所感受与欣赏,从而远去“世情”,获得“生”的慰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这首诗很美,美就美在,这是一幅完完全全纯自然地、无意识地反映陶渊明人生追求的画面,更妙的是连他也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正如庄子所谓的人生至境,真正的自由乃是“无所待”的自由:“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上与造物者游。”{11}这才是一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逍遥游。这是一种无我,也是一种最佳的“天人合一”。
综观陶渊明屡隐屡仕的一生,他达到了一种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他领悟到大自然的不息生机是自己最好的安归之处,于是完全融入到自然中去。他用朴素的“田家语”去表达自然,而自然的大美却从心里流溢出来。因为他不像中朝名士那样模山范水,也不像江左名士那样有距离地欣赏自然,而是把自己化入自然,寄意自然,又游心于自然之外,心境与物境完全融为一体。这是玄学的最高境界,玄学家没有达到,陶渊明达到了。“结庐在人境”的他,面对贫穷,以儒家安贫乐道的精神处之,有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的高尚情怀和宁静心境;面对人生苦患,他以老、庄无为的玄学人生观和“游世”的思想“放意与天游”,以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使人的心灵获得自由解放,真正达到“心游”和“乘物以游心”的精神状态。
{1}{2}{3}{6}{8}{11} 付云龙、陆钦:《老子·庄子全文注释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第165页,第396页,第143页,第165页,第468页。
{4}{5}{7}{9} 谢先俊、王勋敏:《陶渊明诗文选译》,巴蜀书社1991版,第10页,第23页,第37页,第42页。
{10} 王瑶:《中国文学论丛》,平明出版社1953版,第82页。
参考文献:
[1] 谢先俊,王勋敏.陶渊明诗文选译[M].成都:巴蜀书社,1991.
[2] 冷成金.隐士与解脱[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3] 付云龙,陆钦.老子·庄子全文注释本[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4] 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刘方.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及现代意义[M].成都:巴蜀书社,2003.
[6] 王瑶.中国文学论丛[M].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