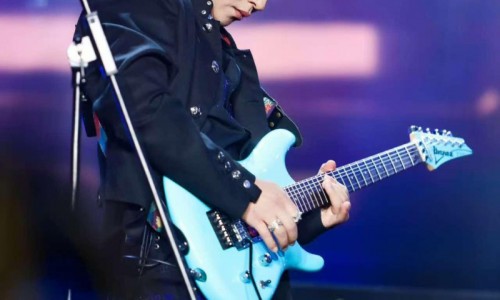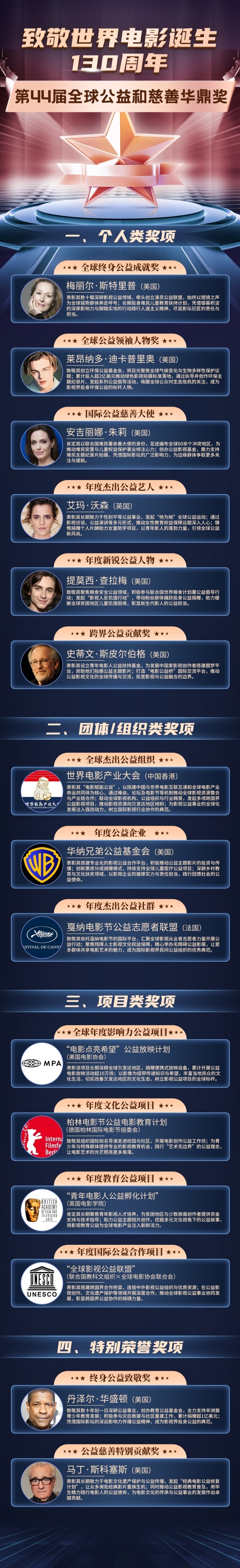... 沉默的经典 露易丝格丽克诗集
刘文
摘 要:在格丽克的诗歌中,美总是不完美的、不完整的、短暂的,在她看来,没有什么可以持久,没有什么是完成的,没有什么是完美的。灵魂必须质疑、必须承受磨难、必须做出抉择,但似乎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决断。
关键词:当代美国诗歌 露易丝·格丽克 生命与永恒
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1943—),当代美国著名诗人,美国国家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1985年的诗集《阿基里斯的胜利》获得全国图书评论家奖,1992年的诗集《野鸢尾》获得1993年普利策诗歌奖,1999年格丽克获得兰南文学奖(奖金十五万美元),1999年至2000年,格丽克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诗歌特别顾问。2001年格丽克获得耶鲁大学颁发的博林艮诗歌奖,她是2003年至2004年度的美国桂冠诗人。2008年格丽克获得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奖(奖金十万美元)。诗集《忠诚之夜,纯真之夜》获得201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格丽克2015年获得美国国家人文艺术院颁发的金质奖章。
一、格丽克诗歌的主题与特点
格丽克的诗歌一直都在追求真实,追问人生的意义。有批评家认为她的诗歌简朴,但过于严肃、残忍与凄凉。她常常书写孤独、悲伤与矛盾,试图从这些探讨中寻求超越以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她认为,这种对难以企及的事物的捕捉是诗歌写作持续的动力,精神上的追求与挣扎就是诗歌艺术的本质。对精神启蒙的欲望有时是可以表述的,但有时却难以言表。因此,格丽克的诗善于捕捉瞬间的感知,从急剧变化的意象中、从日常生活的观察中获得启示与顿悟。格丽克在诗歌中虽然追求完美但无意于得出答案,而是提出问题,诗歌意象倾向于超现实、碎片化。
格丽克的诗歌虽然描写外部世界但意在精神内在,人们可以感觉到内在与外在之间的联系,但诗歌表现的目标是精神、神话与宗教的层次,而不再是日常生活本身。戴维·叶兹评论道:格丽克是个“精神诗人,能够超越感性存在中的残酷现实去寻找人类能够建立精神超越意义的基石”{1}。大卫·奥尔在《纽约时报》书评专栏写道:“格丽克的诗歌是梦幻的、阴冷的、谜一般的;是静默的、极简的。诗歌中常常使用‘阴暗‘池塘‘灵魂‘身体‘大地等词语。语气精致的变换犹如海鸟拍动翅膀飞翔数百英里那样产生的效果。她的诗歌更多依赖的是氛围和暗示:她不是场景描写大师,但却是场景设置大师;这些场景往往是阴暗的。”{2}
格丽克1985年的诗集《阿基里斯的胜利》较多使用古典神话和《圣经》典故作为诗歌的背景,淡化个人色彩,因此在表现欲望主题时显得较为坦率直言、毫不隐讳。这部诗集主要探讨欲望与自由、欲望与权力、爱欲与艺术,体现出女性在面对欲望时的被动与无奈。然而,通过神话所表达的不仅仅是神话本身,还有与当代生活紧密相连,突出表现个人的内在精神生活和外部社会生活。哈佛大学著名诗歌评论家海伦·文德勒指出,格丽克的诗歌“以沉着冷静的语气讲述了伊甸园里的男女,讲述了达芙妮与阿波罗,讲述了神秘的动物。然而,在这些故事的背后却盘旋着作者萦绕于诗歌中半透明的心理状态”{3}。丹尼尔·莫里斯也认为,“格丽克用神话人物作为伪装,创造了具有公众意义的个人叙事”{4}。格丽克诗歌中具有简单与深奥的悖论,在她的静默中却存在着难度和精妙的天赋。她的诗歌善于描述那些内心冲突、挣扎的情感,这些情感都是人们不轻易承认的一种存在,但格丽克却通过自己的诗歌努力解决、设法克服。她的诗常常来源于自己的生活,但通过细节描写、抽象提炼以及使用神话典故而有了更广泛的意义。
二、野鸢尾:生命的力量
格丽克的诗集《野鸢尾》以三种声音,即花说给人类的声音、人说给上帝的声音以及上帝说给人的声音述说,表达诗人对于宗教和死亡的矛盾情感;诗歌直面人生的恐怖、艰难和痛苦,以阴暗的自然意象反映她无助、被背叛和失落的情感。鸢尾花大而美丽,叶片青翠碧绿,犹如美丽的女王,矗立在花丛中,等待着人们来欣赏它的美艳。鸢尾花还有彩虹之意,象征彩虹女神,是众神与凡间的使者。鸢尾花太美丽了,不仅飞禽走兽和蜜蜂爱恋她们,就连轻风和流水都要停下来欣赏。然而,在格丽克的诗歌《野鸢尾》中,诗人描写的不是野鸢尾美丽的外表,而是野鸢尾经历的炼狱般的生命考验以及新生命喷薄而出的力量。
在《野鸢尾》中,诗人把人类的痛苦与野鸢尾的生长过程相比较。野鸢尾冲破坚硬的大地,从另一个世界、从地下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旅程,来到人世间。野鸢尾花朵的深蓝色代表了新的生命。亨利·科尔认为,“格丽克的诗歌中,生命持续地反映在季节的变幻中。自我、灵魂在体内苏醒,犹如开花的李树一样会随着秋天的到来而凋谢”{5}。当“微弱的太阳光/闪烁在干枯的地表”,野鸢尾倾听着上面“松枝变幻”,她的灵魂清醒地意识到“被埋在黑暗大地”的感觉,然后意识到“坚硬的大地/微微弯曲”,“感觉似鸟儿的东西在低矮的灌木丛中疾速飞驰”。这些强调的是野鸢尾在经历了一个冬天之后从地下到地面时对外部世界的最初认知,表达她从地下显现出来的感觉。当野鸢尾从被遗忘的状态返回到这个世界为自己寻找一个声音时,她感觉到“一个巨大的源泉”从心中喷涌而出,以其“深蓝的身影投射到蔚蓝的海上”,此时的野鸢尾不仅以美丽的花的形式出现,还以其喷涌而出时发出的巨大声音宣布了她的重生。从“痛苦的终点”,从“人们称之为死亡”的地方,从“沉寂”中,从“被埋在黑暗的大地”,从“作为灵魂,不能说话”的被动状态,到“坚硬的大地”的萌动,然后经历这“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行程”后,她感叹:能够“活下来真难”!现在,她回来了,而且还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她生命的中心发出一个强大的声音,以自己巨大的“蓝色身影投射到蔚蓝的海上”。这个奋斗的过程、这个奋勇挣扎的过程就是一个孕育的过程和结出硕果的过程,也是一个突破束缚寻求解放的过程,当然这也是对野鸢尾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的歌颂。在这个过程中,她有过“痛苦”和“害怕”,有过“死亡”的威胁,但毕竟“有一扇门”,有不死的“灵魂”。“鸟儿”的形象表明她拥有对飞翔的渴望,在生命的中心还有一个“巨大的源泉”,野鸢尾的生命历程确实是一曲伟大的生命之歌。
三、银百合与金百合:短暂与永恒
在诗集《野鸢尾》的最后有几首关于百合的诗,包括《金百合》《银百合》和《白百合》。在《银百合》中,说话者银百合悲叹自己面临死亡的命运,“我将看不到下个满月”。从早春到晚秋(“一串串的枫树籽落下”),银百合与它的女主人(园丁)已经相伴很久,然后银百合转向女主人,问她与丈夫在一起的结局,问她是否知道终结的含义。女主人其实已经借银百合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即将破碎的婚姻的态度:“我们已经向着尽头走得太远/以至于不再害怕尽头。”
诗歌《金百合》以花的声音说给人类,也可能说给上帝。当金百合面临死亡之时,它祈求生养它的人或者上帝能够拯救它,但没有得到回应。当诗歌赋予无声的百合以声音时,诗歌也赋予死亡前夜的人类以声音,只是人类呼求的对象似乎没有听到,或者不愿意倾听,又或者这个呼求的对象根本就不存在。因此,诗歌讲述的是生命最大的恐惧——死亡。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讲述的内容就是为死亡而做的准备,是如何面对死亡、面对终结。
百合是多年生植物,每年都会按时开花。百合花在面临死亡到来之时发出悲叹,一旦枯萎凋谢、落到地上,它就不能再活在这个世上,不能再从大地被召唤回来发芽,“也不再是一朵花,不再是一根荆棘”,它周围的土壤也不再紧紧地围绕着它的肋骨,土壤也不能再把百合从大地破土而出。在百合的周围可能还有其他的百合,他们也同样面临着凋谢枯萎的命运,作为说话者的百合也替它周围的同伴向神明说话,暗示神明也同样没有看到其他百合花的命运。“凋落”一方面指的是死亡,另一方面指的是信仰的失落。根据《圣经·旧约·约伯记》的记载,百合要经受死亡的考验,即考验他们在面临死亡时能否保持他们的信仰。百合祈求主人用拯救他们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怎能知道你能看见/除非你能拯救我们?”诗歌中的“暮光”既指生命的终结也指一天的结束,百合一方面越来越绝望,同时也似乎很谅解自己的主人,想着可能是自己的主人距离较远听不到他们的呼求。百合最后的疑问似乎是在质问:难道你不是我的父,难道不是你把我抚养?前一句只是怀疑主人离百合太远可能听不到,但这一句实际上是在怀疑这位主人的身份:这位主人究竟是不是它的父?百合作为夏末凋谢的植物与较早开花的野鸢尾在诗集中首尾呼应,野鸢尾是破土而出,百合是凋谢枯萎。金百合中的“金”指的是与永恒相关的颜色,而百合却面临着死亡,因此,金百合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纯洁、无辜、无罪的百合之死暗示生存的残酷。
{1} David Yezzi. Louise Glücks Dark Visions. Sewanee Review 120.1(2012):105.
{2} David Orr. Louise Glücks Metamorphose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an 20, 2013:14.
{3} Helen Vendler. Soul Says: On Recent Poet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95:16.
{4} Daniel Morris. 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 A Thematic Introduction. Columbia, MO: U. of Missouri Press, 2006:3.
{5} Henri Cole. Louise Glücks “Messengers”.Daedalus 143.1 (2014):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