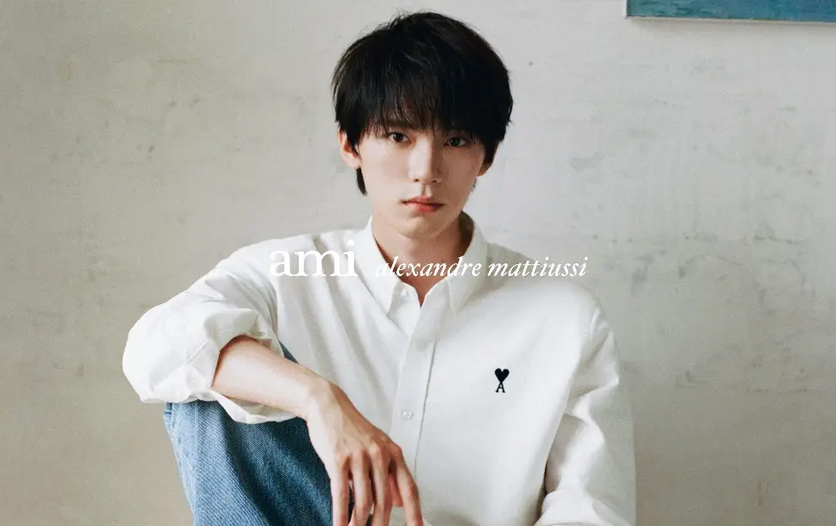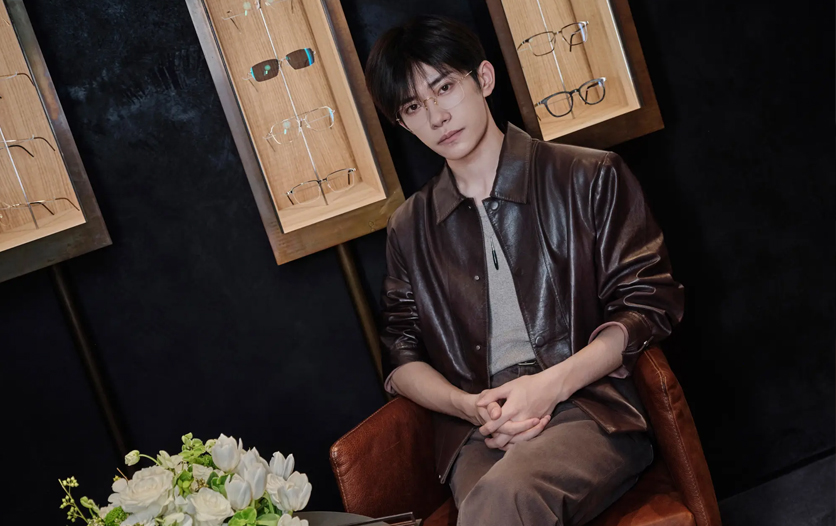哲学地历史哲学地历史片16,哲学地历史片16下载,哲学地历史...
王平
摘 要:新历史小说表现了作家把握历史话语权时的主体能动性,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使文本的哲理空间得以深刻拓展。
关键词:新历史小说 价值 质疑历史 哲学反思
对于任何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来说,如果没有作家价值观的观照,它不能成为一个文学文本;只有通过作家主题的确立、人物的塑造、叙事策略的选择等艺术手段,才能把这些因素演绎为一个个历史故事,即历史小说。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悲剧性的事件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喜剧性的”{1}。
历史叙事的背后体现了作家的价值追求,它直接影响人观照历史的观念和方法,决定着历史叙事的目的和方向;不同的价值追求,往往导致千差万别的历史叙事风格。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学叙事中,由于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文以载道”成为中国文学的永恒使命,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学创作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诉求,这也形成了中国历史小说道德中心主义的评判传统。作者大多以统治阶级的立场、正史或官史的视角再现历史,从“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中不难看出封建王权对历史叙事的支配;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更是在统一的政治规约之下,小心地在政治与文学的边缘处行走,稍有不慎即人文俱损。由于创作被规定在有限范围内,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使文学创作在根本上难以有真正个性化的价值追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传统的历史观念处于弱化的状态,在相对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下,作家力求通过作品表达对历史表象下真实本质的追寻,并尝试以多元的历史叙述功能,颠覆曾被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下的历史观。新历史小说则充分表现了作家把握历史话语权时的主体能动性,他们对于已经被意识形态以教科书和官史等形式固定下来的过往历史事件,以前所未有的打破一切之勇气进行质疑与颠覆,他们在历史的缝隙处,洞见种种荒诞与谬见,表现出更强烈的问题意识,使文本的哲理空间得以深刻拓展。
新历史小说作家的主体精神首先表现为对现有自在的历史采取了一种怀疑的姿态,正如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2}新历史小说作家怀疑过去为人们所承认或膜拜的“历史本身”的客观真实性,并质疑它的权威性:苏童困惑于“人与历史的距离亦近亦远。我看历史是墙外笙歌雨夜惊梦,历史看我,或许就是井底之蛙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呢?”{3}余华强调:“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4}李锐表示:“我想把那些被无情泯灭的生命从历史的谎言中打捞出来给人看。”{5}格非感慨作家“对历史的自信与执着恰好构成了对其自身境遇的反讽”{6}。这些都表达了作家对历史话语一元化格局的怀疑。
出于对信仰的怀疑与对真理的筛选,新历史小说作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便是为历史去蔽;在创作的时候,作家尝试从自己的视点出发,以主动介入历史的姿态,通过对历史边角余料的重新组合编码,对历史进行独特的虚构,他们笔下的历史图景并不仅仅是恢复或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呈现出多元的个人风格,即“重要的不是写作,而是通过写作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7},与以往历史小说作家显示出了巨大的时代差异。
比如《传说之死》中的六姑婆只是出于对死去父亲的忠孝,在劝说弟弟退出革命无效的情况下,茫然地从一个吃斋念佛的女人变成了一个地下党员,目不识丁的她对革命的理解只是“多少年了,这个城里就是这样杀来杀去的……”而在六姑婆带着她的传说死去之后,被作为这座城市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载入了史册,人们在借这位“进步女性”炫耀着该市历史的传奇色彩时,对历史的真相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历史的真相永远被六姑婆带走了,所有的传说只能距离这真相愈来愈远,正如作品在收尾时写道:“但那都是和六姑婆无关的传说。”乔良在《灵旗》中直面红军征战史最惨烈最悲壮的第一次大败仗,对冷冰冰的正史“湘江一战,损失过半”进行了重新叙述:“离开红都瑞金时尚有八万余众的红军,是役后仅存三万。”他拨开沉重的历史之手,于缝隙间追寻人性世界最隐秘的颤动,思考极限中的体验与挣扎。尽管在这一颠覆与重建的过程中,有时候也会矫枉过正,正如苏童在谈到他的《米》时所说:“小说有时就是一次无中生有。就像《米》中的人物,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五龙这样坏的人……写《米》这部小说,我感觉像是在做数学,在做函数。为什么呢?我在推断一种最大值。所以我觉得《米》的写作是非常极端的……因为这是我对于人性在用小说的方式做出某一种推测,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到最极致,是负方向的,反方向的。”{8}任何一种演变都很难做到以绝对理性的频率循序渐进,解构对结构的摧毁与撼动也不是有规律地进行,正如王尔德的慨叹:“一个需要修补的世界被一个无法修补的世界代替了。”
新历史小说作家对历史的叙述超越了党派、政治、阶级之类的观念,从哲学高度进行终极思考。哲学并不是如星星般只悬浮于人类精神的高空,而是要诗意地栖居,新历史小说文本中处处闪烁着哲学思想的光辉。
正如莫言所说:“对故乡的超越首先是思想的超越,或者说是哲学的超越,这束哲学的灵光,不知将照耀到哪颗幸运的头颅上,我与我的同行们在一样努力地祈祷着、企盼着成为幸运的头颅。”{9}苏童也认为:“作家们在借助写作探索自己的哲学观和道德观。”{10}新历史小说作家在历史面前以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和优越感,把存在于典籍中的历史虚化为一道风景,通过自己的话语叙述,将历史重新编码,使新历史小说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事件本身,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哲学高度,与新时期西方哲学思想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有着相通之处。新历史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潮有异曲同工之处。现代主义思潮尽管早已在20世纪初传到中国,但却是在80年代末空前热闹,同一时期兴盛起来的新历史小说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新历史小说注重审丑的挖掘,注重表现人的失望、焦虑与孤独,体现了“现代性”价值的追求。新历史小说作家对既定历史持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和否定意识,也与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加缪、海德格尔等人产生某种精神暗合,“表现了颇浓重的存在主义思想倾向”{11}。
新历史小说表达的主题之一便是人的“荒诞生存”,人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是一个荒谬的存在,他们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永远只能忧虑和恐惧,如格非的《迷舟》、余华的《活着》《在细雨中呼喊》《鲜血梅花》《古典爱情》、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李锐的《旧址》等都体现了这种人生的荒谬与苦痛,这正是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思想表征。存在主义认为人孤独地在荒诞的、不可理解的世界上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萨特在《厌恶》中指出,存在是“虚无”的,现实是“恶心”的,一方面“他人就是地狱”,另一方面人又无法离开他人单独存在,因此悲剧不可避免,无处不在,道破了人生悲剧性的真相。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小说家加缪作为“荒诞哲学”的代表,他的《西西弗的神话》的副标题就是“论荒谬”,加缪认为人的荒诞感产生的原因是:“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像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12}新历史小说的哲学精神虽然传承于存在主义哲学精神,但存在主义面对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的矛盾和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对人异化的加剧,它注重人的主观经验,从根本上否认一切人生价值,是一种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新历史小说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存在主义的质疑现实的精神,从根本上说它没有西方的文化根基。
当然,新历史小说作家在吸取借鉴现代主义的哲学精神、文学观念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有所突破,作品呈现出某些后现代主义倾向。他们不再以精英姿态承担崇高神圣的社会职责以追求文学的终极价值,他们怀疑崇高否定理想,以暴力、死亡等内容展示人生的荒诞,作品充满了颓废、绝望的情绪。可以说,新历史小说作家从哲学高度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从文本叙事上进行了革命性的探索,才最终导致了与“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彻底的决裂。这既是新时期小说文体形式内在发展的必然,也表现出新历史小说作家希望与世界文学同步的愿望。
{1} [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164页。
{2} [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3页。
{3} 苏童:《苏童文集·后宫·自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4} 余华:《虚伪的作品》,《余华作品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5} 李锐:《银城故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6} 格非:《小说艺术面面观》,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页。
{7} 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8} 苏童、张学昕:《回忆·想象·叙述·写作的发生》,《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期。
{9} 莫言:《超越故乡》,《名作欣赏》2013年第1期。
{10} 张清华:《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及美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42页。
{11} 吴秀明、刘起林:《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0页。
{12} [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