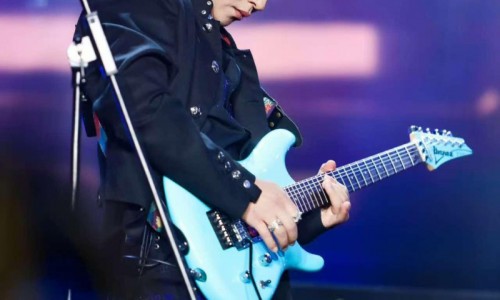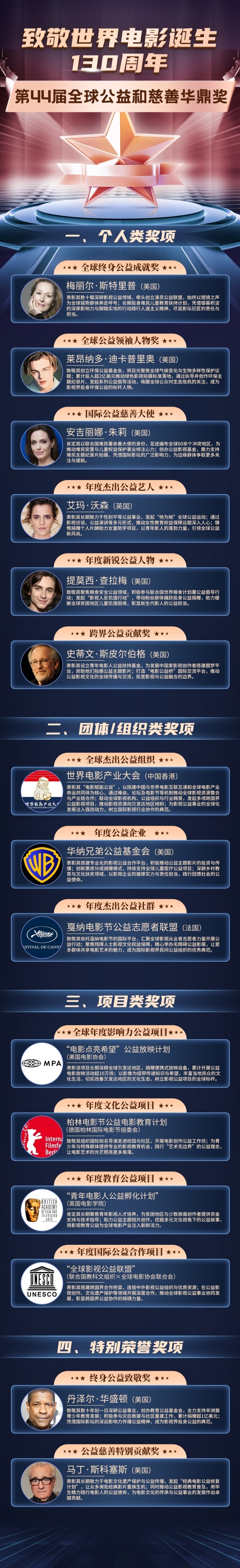人在樊笼,心在岛上 印尼巴厘岛归来
董晓菲
摘 要:关于“庄周梦蝶”,历来阐释不一,本文通过对古典诗词中梦蝶典故的简单梳理,试从两个方面略加分析:第一个以“梦”为支点,陈述梦醒了无路可走;第二个则以“化”为支点,陈述梦醒了世界光亮,并由此引出庄子梦蝶的真正归宿——心,进而指出庄子的“愚民”思想,实际上是“愉民”,其目的在于号召人们去除我执,回归本心。
关键词:庄周梦蝶 “愚民” “愉民” 回归本心
《庄子·齐物论》云:“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在这里,庄子以梦蝶为依托,借以表达“物化”的思想,在他看来,“周与蝶则必有分”,但二者又可以互相兼容,成为一个不辨你我的合而为一的状态。他把这一融合的状态安放在梦这个大的背景里,其不可控的成分便凸显出来,大致走向有以下两种。
一、梦醒了无路可走
梦属于灵魂医学范畴,是一种不自觉的虚拟意识,是一种主体经验,其成因与人的社会环境、心理因素以及形体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庄子》一书中有多处提到楚王派使者恭请庄子入朝为官,庄子每次都予以拒绝,在他看来,与其在浑浊的乱世为官,享世人所喜之富贵荣华,最后落个不善而终,倒不如自在游荡于安宁的内心,品他人所贱之贫困沧桑,最后却得个乘物游心、颐养天年的好去处,所以他拒绝做那披红挂彩受人拜祭的神龟,而要做曳尾涂中的平庸之龟。所以,在世人看来,庄子总是陷于贫困之境,形容枯槁,这是他的形体风貌,但他却又有屈原一样“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逍遥自在,之所以有这样的对比,恰恰是因为他所处的社会是一种离乱、战乱、纷乱不止的境况,而像庄子这种感受力比较敏锐的人,他比大多数人更能体悟到这种荒乱,并且看得更加透彻。
以这样的人生境遇为依托,庄子的梦刚好与之形成一种本能的反差,外围的世界荒乱,梦中的景象安宁,外在的利害束缚着身躯,内心的逍遥却羽化了身躯,所以,他的梦与现实搭上联络,这是庄子的梦,梦中不辨蝶与我。
梦有很多种类型,象梦是其中一种。所谓“象梦”,即梦意在梦境内容中通过象征手段表现出来。庄周梦蝶,实际上就属于象梦,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人是无法变成蝴蝶的,蝴蝶象征的恰好就是现实中得不到的自在状态,它充分彰示了人对“自由”的向往。不过,既然梦是幻觉、妄想,具备不确定、不协调,或者不可实现的特点,所以,在众多人对于“庄周梦蝶”的释义中,不难引出梦的最终结局——空寂。试看下列诗词:
辛弃疾《兰陵王·己末八月二十日夜》:“寻思人世,只合化,梦中蝶。”
《念奴娇·和赵国兴知录韵》词:“怎得身似庄周,梦中蝴蝶,花底人间世。”
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四折:“惊觉我的是颤巍巍竹影走龙蛇,虚飘飘庄周梦蝴蝶。”
韦庄《春日》诗:“旅梦乱随蝴蝶散,离魂渐逐杜鹃飞。”
马致远《夜行船·秋思》曲:“百岁光阴如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
陆游《病后晨兴食粥戏书》诗:“蝴蝶庄周安在哉,达人聊借作嘲诙。”
陆游《冬夜》诗:“一杯罂粟蛮奴供,庄周蝴蝶两俱空。”
李中《暮春吟怀寄姚端先辈》诗:“庄梦断时灯欲烬,蜀魂啼处酒初醒。”
在这些诗词中,表达了一个较为统一的主题就是梦为幻境,梦醒时只有无边的空寂,梦做得越好越完美,醒过来的现实越差越冰冷,因为人对于现实是无奈的,人无法改变现状,只能听之任之,煎熬着了断残生。所以他们认为庄子用梦虚构了一个理想的充满自由快乐的乌托邦,却让人醒时陷入更为禁闭悲哀的深渊,所以他们把阐释的重心放在了消极的梦与现实的落差感上,认为人生最终还是悲凉,梦醒了却无路可走。
二、梦醒了世界光亮
庄子的“物化”认为物与我虽有分别,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为一,也就是中国人追逐的天人合一、玄同彼我的状态,在这种思维走向里,人们把释梦的着眼点放在了“化”这个字眼上,最终以美好为归宿。所谓“化“,郭象说:“愚者切切然自以为知生之可乐,死之可苦,未闻物化之谓也。”也就是说,“物化”取消了物我的差异,世间事无生之乐,无死之苦,区别是根本不需要的,甚至说是愚笨之举。这也就是陈鼓应所说的“物我界限之消解,万物融化为一”。这种物我合一的状态,刘武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栩栩然者蝶也,蘧蘧然者周也。魂交则蝶也,形接则周也。故曰:‘则必有分矣。然蝶为周所梦化,则周亦蝶也,蝶亦周也,分而不分也,即‘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也就是《庄子·齐物论》所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这种物化的状态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直接的思维走向是人们总是以为化为蝴蝶之后可以找到自由,无拘无束,悠然自得,因为在人们的心底总是觉得蝴蝶翩翩飞舞,不受约束,生命绽放的程度似乎是随心所欲的,所以,人如果化为蝴蝶,就可以抛掉自身的负重,活得轻盈自在。试看下列诗词:
黄庭坚《次韵石七二七首》之六:“看着庄周枯槁,化为胡蝶轻。”
黄庭坚《古风次韵答初和甫二首》之二:“道人四十心如水,那得梦为胡蝶狂。”
陆游《睡觉作》诗之一:“但解消摇化蝴蝶,不须富贵慕蚍蜉。”
黄庭坚《煎茶赋》:“不游轩后之华胥,则化庄周之胡蝶。”
刘兼《昼寝》诗:“恣情枕上飞庄蝶,任尔云间骋陆龙。”
卢肇《湖南观双柘枝舞赋》:“帽莹随蛇,熠熠芝兰之露;裾翻庄蝶,翩翩猎蕙之风。”
徐夤《初夏戏题》诗:“青虫也学庄周梦,化作南园蛱蝶飞。”
在这些诗词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蝴蝶翩飞,自在不过,所以人若化蝶,便可以抛开俗世的烦恼忧愁,在天地间自由驰骋,收获一片光亮明媚的风景。人们把梦蝶的举动当作一种对自由的向往,虽然现实的生活是苦涩的,但梦中的景象却是灿烂的,这也成为一种生活的动力,为了自由的未来忍受现在的捆缚,人们怀着期待看着蝴蝶跟人合而为一,所以,梦醒了,世界反而光亮许多。
事实上与人相比,蝴蝶更不自在。蝴蝶的生长周期要经历卵、幼虫、蛹和成虫这样四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要小心翼翼。而成虫之后,又要面对各种天敌,比如蚂蚁、甲虫、鸟、蝇、蜥蜴、蛙、蟾蜍、螳螂、蜘蛛、黄蜂,等等,在受外来威胁的同时,又因为自身身体的特质,受到环境的影响。蝴蝶是变温动物,体温会随周围环境不断变化,生命活动因此也直接受到外界温度的支配,温度一低就要停止活动,所以,在海拔3000—4000米的高山上,当太阳从云层突出而光热照射到大地的时候,蝴蝶才会四处翩飞,但是当太阳被云层遮蔽,即刻会停止活动,然后踪迹全无。所以蝴蝶生活的区域很有限,它们喜欢生活在草木繁茂、鲜花怒放、五彩缤纷的阳光下,上下飞舞盘旋,并以采食花粉和花蜜为生。有资料表明,蝴蝶的寿命长短不一,但长的也只不过11个月,短的甚至2—3个星期,并且在这短暂的生命里,雄蝶又要忙着寻找雌蝶交尾,雌蝶则要找寻寄生产卵,活动频繁,以此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
自然如此规定了蝴蝶的生命形式,强大的自然规律成了不可抗力,而除了它飞舞的翅膀,它根本没有额外的自由可言。所以,庄周梦蝶并非要变化成蝶,而只是以蝴蝶为寄托,表达“乘物游心”的意志,所以才有了一个与孔孟儒学完全不一样的思维转向,即对“心”的重视,主体的人受到关注之后,支配人活动的“心”自然而然就要得到相应的照料,身体即使无法羽化,心灵却可以登仙,所以才有了“心斋”“坐忘”这些智慧思维的结晶。庄子说:“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也就是说,人的身躯虽然受到现实的劳役,不可随意妄为,但作为主宰身体的心灵却可以任由自我操控,庄子用他的实际行动告知我们,这种“愚民”行为是有益处的。
我们通常所说的“愚民”如指人,即为愚昧无知之民,如指行为则是说使人民变得愚昧无知。在这个意义上,会出现两种对立的势力,即统治者和普通民众,统治者用尽一切办法来使民愚昧无知,以此来巩固他的统治,即上对下的权利压制,且这种压制具有强烈的压倒性和不可冒犯性,所以,这种“愚”是“愚昧无知”,是言听计从,是无条件服从。而庄子的“愚”则应该是“娱”或“愉”,因为作为主体的人如果想要回归最初的本心,他就必然要放弃智巧,放弃争名逐利,学会舍弃,也就是“去执”,没有执着,便没有烦恼,身躯不受名利所累,心灵才能羽化登仙,“愚民”者,内心愉悦者也,如赤子般诚挚,如孩童般天真。钱起《衡门春夜》悟得好:“寄言庄叟蝶,与尔得天真。”这才应该是“庄周梦蝶”真正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杨义.庄子还原[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 陈鼓应.庄子浅说[M].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
[3] 傅佩荣.傅佩荣译解庄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4] 杨立华.郭象《庄子注》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 陈晓鸣等.中国观赏蝴蝶[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