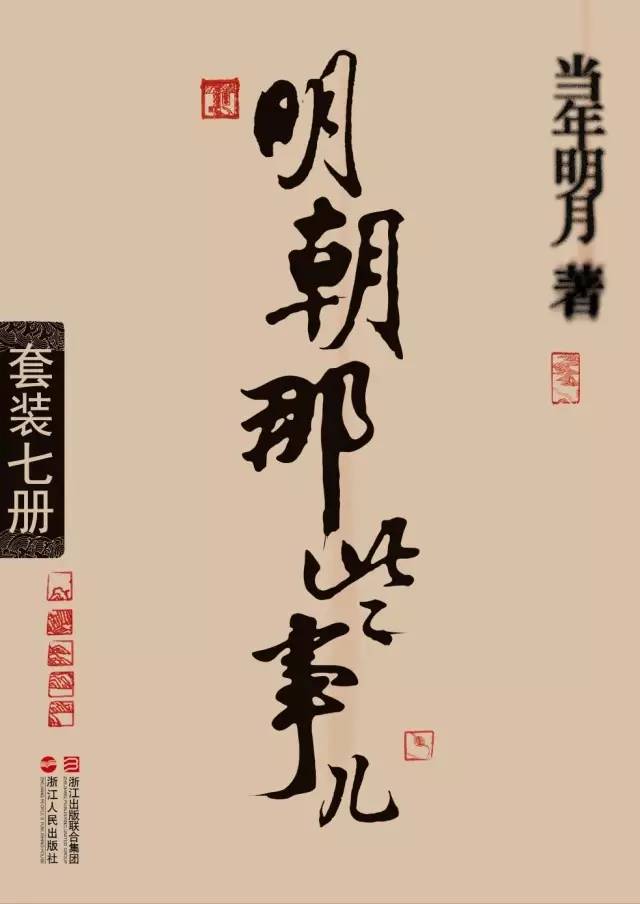
豆瓣评分最高的历史小说
摘 要:新历史小说挣脱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通过书写历史来关注个人,作家将目光投向历史的各个角落,从自然困境、社会困境、精神困境三个角度揭示人的现实境遇。
关键词:新历史小说 个人 生存困境
文学是关于人类灵魂的艺术,文学自它诞生以来,就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勃兰兑斯在《19世纪文学主流》中曾经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1}
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对‘人的不断发现,‘人的观念的不断发展,是百年中国文学发生的最根本的变化。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核心内涵”{2}。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文学以揭示人性为核心任务,关心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境遇。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中国稳定的传统根基和强大的文化惯性,人的主体性始终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小说中出现的多为本质上是集体性的人,“集体性确实是某种人类的事情,但它是一种没有人的人类,是没有精神的人类,是没有灵魂的人类……”{3}在集体性的掩盖之下,所有涉及感官和个体情感的内容均遭到排斥,感性的人消失,变成一个没有所指的词语空壳、一个同一的理性符号。
新历史小说就是对这种潜流的响应,它挣脱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通过书写历史来关注个人,因而,新历史小说作家将目光投向历史的各个角落,从野史、艳史、趣史、外史中寻找人的存在,恢复和再现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具体的人性。无论是人类、民族还是整个国家的诞生与发展,都并非是一路坦途,总是充满曲折和跌宕,这是历史与生俱来的特性。“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4}人在历史中的生活还包含了历史造就的人生的荒谬。
新历史小说主要从三个角度揭示历史中人的生存困境:自然困境、社会困境、精神困境。
新历史小说对自然困境的描述大多体现在“饥饿”主题上。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匮乏造成了物资匮乏,尤其是旧中国约有五分之四的人口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饥饿已经作为我们民族的整体记忆继而演变为历史叙事的母题,比任何文明形式都更能接近生存的本质。在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中,人始终处在战乱和饥饿的威胁之下,医学院校花乔其莎和留学俄罗斯的霍丽娜只为了一点吃食就能向炊事员献出身体;为了活下去,母亲卖了七姐,并眼看着四姐去卖身;玉女为了不让母亲吐粮食养活儿女投河自杀。
作家苏童欲“看清人性自身的面目,来营造一个小说世界”{5},他的小说《米》的主人公五龙由于洪水与饥荒被迫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周遭邪恶、淫乱、战争、压迫等织就的天罗地网激发了五龙的人性之恶,他用以恶抗恶的方式,最终成为瓦匠街的黑社会头目,然而这一切并未使他的内心得到安宁,最后死于他乡之路。这种关于“吃”与“食”的饥饿在许多新历史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由于瘟疫和饥荒,女人们变得凶恶暴虐,她们几乎每天都在死人塘边因争夺野菜而争吵斗殴,祖母蒋氏还挥舞圆镰砍伤了好几个乡亲;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中人们忍饥挨饿,吃树叶吃树皮吃草根,吃玉米芯、谷穗、榆钱、椿叶,“阳光照着他们霉中透绿的脸,阳光很鲜活,可是阳光是不能吃的”。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通过对一场大灾荒的追述,表达了对人的苦难生存的悲悯。1942年河南旱灾和蝗灾导致三千万人受灾,三百万人饿死,所有能吃的已吃光,即便是吃后让人四肢麻痹的野草“霉花”都成了“佳肴”,然而死亡与绝望仍旧如影随形:死在逃荒路上、卖儿鬻女、女孩沦为娼妓,甚至人吃人……
新历史小说对社会困境的描述主要表现在国家机器对人的倾轧。新历史小说作家深切地关注历史上卑微的普通个体,尤其是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他们身处在历史的巨大的漩涡之中,历史的谬误造就了人生的谬误。
余华《兄弟》中的宋凡平,因为要去上海接生病的妻子李兰,被误认为要逃跑,“红袖章”们竟然当众拳打脚踢,把木棍插进他的身体,最后活活把他打死。宋凡平死后因为身体无法平整地放入棺材,下葬的人把他的腿折断后,用砖头用菜刀用各种东西砸碎了他的膝盖和骨头。在那个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年代里,死和生同样没有尊严。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以个人生活史的叙述勾勒了乡村社会图景。小说中赵北存因为种出一根又长又粗的玉术棒子受到了国家领导的接见,这个带来巨大荣誉的玉米棒给赵北存的妻子招娣带来了祸患,她因为过度小心谨慎竟失手使玉米跌落破裂;招娣在惊恐不安中死去。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常常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生活,被社会的激流裹挟着不停地运转,直至失去了自我,就像埃里希·弗洛姆所说的:“在这种体验中,个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或者说,个人在这种体验中变得使自己疏远起来”{6},当强调人的阶级性而否定人性的普遍性时,被扭曲的灵魂便上演了一出出人性的悲歌。尤凤伟的《远去的二姑》便表达了作者对战争背后的人性隐秘的探求。不到三十岁的财主少爷宋吾健是个读书人,后来当上伪县长;二姑是他的未婚妻,在抗日救国军的说服下,二姑进城诱使对她满腔热情的未婚夫出城护送。最后宋吾健被枪毙,大义灭亲后二姑无法摆脱内心的痛苦,从此失踪,也许悄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社会的挤压下,人失去了对自己的所有权。
新历史小说对人精神困境的描述主要表现在人在历史中的异化。所谓异化是指人“对所造之物和环境的屈从”{7},在功利化的生存境遇下,人在飞速运转的国家机器挟持下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日渐麻木,从余华小说《活着》的主人公福贵的遭遇可见一斑。地主少爷福贵年轻时嗜赌,因为输光了家产沦为贫农,躲过了解放初期的土改一劫,但死亡一直如影随形地追逐着这个家庭。母亲病死,儿子有庆为了给县长老婆献血被医院活活抽血而死,女儿凤霞难产而死,妻子家珍长年劳作终于累死,女婿二喜被工地上的水泥板夹死,唯一的外孙苦根因为过于饥饿吃豆子胀死。他的亲人不是死于时代造成的贫病交加,就是死于一种社会政治势力,奇迹般活着的只有福贵,而他竟也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样的命运。《从两个蛋开始》中只因赵北存是符驮村的掌权者,他什么时候想睡哪个女人就到人家里给她的男人派活挣工分;男人们乖乖地出去,女人们主动奉献身体,任他胡作非为。为了多分粮食解决吃饭问题,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毫无人的尊严,为了生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兰德曼认为:人是历史的存在。新历史小说这种对人的生存困境关注的背后,实际上蕴含了作家的价值追求。如果说革命历史小说中展示了革命年代人们在政治激情遮蔽下被迫压抑原始生命本能,转向革命理想主义的激情,那么新历史小说则更多地告诉人们,在基本的生存条件、起码的生活需求得不到保障的年代,人整个生命甚至灵魂是如何被吞噬被毁灭的。这也正合了美国新历史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森的话,这种个人命运“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8}。那么,在这种悲剧性的生存困境之中,人难道只能如传统型历史小说那样只有唯一正确的选择吗?新历史小说以纷纭的历史事件和复杂的人物形象,道出了多种选择的合理性存在,与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名剧《死无葬身之地》所揭示的哲理如出一辙。
《死无葬身之地》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抵抗运动为背景,讲述了游击队员被逮捕之后,在拷打与酷刑中,心中的爱情、亲情、恐惧、信任、背叛、绝望等元素此消彼长,最终在极限中做出各种选择:索尔比埃在被提审时,怕自己因为胆小招供,于是就借了一个机会跳楼自杀了;希腊人卡诺里斯一声不吭挺住了;昂利非常骄傲,但是他依然喊出了声,他为此感到了羞愧;女队员吕茜被提审的时间很长,直到她回来,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连她的情人让去安慰她,都遭到拒绝,她被强奸了;吕茜的弟弟十五岁的弗朗索瓦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下产生了动摇心理,在他尚未决心供出实情时,吕茜让她的伙伴掐死了他。这些革命者并没有被刻画成顽强不屈的英雄,他们也有私心杂念,也有绝望与恐惧,然而,人在现实境遇中的选择是自由的,同实现人的价值密切相关。历史并不是一潭清澈而透明的湖水,而是乱象纷呈,复杂而诡异。
新历史小说作家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了世界的荒诞和生存的荒谬,正是在既定的悲剧主题下,通过设置荒诞的生存处境,把被“群众”“人民”遮蔽下的人解放出来,把打上了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事件恢复到原初的面目,借历史传达自己的现代意识,从而颠覆那种由简单阶级论与进化论模式搭建起来的删除真正个体处境的宏伟历史构架。■
■
{1} [丹]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 朱栋霖:《比较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3} [美]弗莱德·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4} [德]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61—462页。
{5} 苏童、周新民:《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苏童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6} [美]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20页。
{7} [美]埃里希·弗洛姆:《人的希望》,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8}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载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L16BZ
W009)阶段性成果
作 者:王平,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编 辑:张晴 E?鄄mail:zqmz0601@163.com









